|
当它安置辐的时候,我们只见它向各个方向乱跳,似乎毫无规则,但是这种无规则的工作的结果是造成一个规则而美丽的网,像教堂中的玫瑰窗一般。即使他用了圆规、尺子之类的工具。没有一个设计家能画出一个比这更规范的网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扇形里,所有的弦,也就是那构成螺旋形线圈的横辐,都是互相平行的,并且越靠近中心,这种弦之间的距离就越远。每一根弦和支持它的两根辐交成四个角,一边的两个是钝角,另一边的两个是锐角。而同一扇形中的弦和辐所交成的钝角和锐角正好各自相等——因为这些弦都是平行的。
不但如此,凭我们的观察,这些相等的锐角和钝角,又和别的扇形中的锐角和钝角分别相等,所以,总的看来,这螺旋形的线圈包括一组组的横档以及一组组和辐交成相等的角。
这种特性使我们想到数学家们所称的“对数螺线”。这种曲线在科学领域是很著名的。对数螺线是一根无止尽的螺线,它永远向着极绕,越绕越靠近极,但又永远不能到达极。即使用最精密的仪器,我们也看不到一根完全的对数螺线。这种图形只存在科学家的假想中,可令人惊讶的是小小的蜘蛛也知道这线,它就是依照这种曲线的法则来绕它网上的螺线的,而且做得很精确。
这螺旋线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用一根有弹性的线绕成一个对数螺线的图形,再把这根线放开来,然后拉紧放开的那部分,那么线的运动的一端就会划成一个和原来的对数螺线完全相似的螺线,只是变换了一下位置。这个定理是一位名叫杰克斯.勃诺利的数学教授发现的,他死后,后人把这条定理刻在他的墓碑上,算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迹之一。
那么,难道有着这些特性的对数螺线只是几何学家的一个梦想吗?这真的仅仅是一个梦、一个谜吗?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呢?它确实广泛的巧合,总之它是普遍存在的,有许多动物的建筑都采取这一结构。有一种蜗牛的壳就是依照对数螺线构造的。世界上第一只蜗牛知道了对数螺线,然后用它来造壳,一直到现在,壳的样子还没变过。
在壳类的化石中,这种螺线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在南海,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种太古时代的生物的后代,那就是鹦鹉螺。它们还是很坚贞地守着祖传的老法则,它们的壳和世界初始时它们的老祖宗的壳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它们的壳仍然是依照对数螺线设计的。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就是在我们的死水池里,也有一种螺,它也有一个螺线壳,普通的蜗牛壳也是属于这一构造。
可是这些动物是从哪里学到这种高深的数学知识的呢?又是怎样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蜗牛是从蠕虫进化来的。某一天,蠕虫被太阳晒得舒服极了,无意识地揪住自己的尾巴玩弄起来,便把它绞成螺旋形取乐。突然它发现这样很舒服,于是常常这么做。久而久之便成了螺旋形的了,做螺旋形的壳的计划,就是从这时候产生的。
但是蜘蛛呢?它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呢?因为它和蠕虫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它却很熟悉对数螺线,而且能够简单地运用到它的网中。蜗牛的壳要造好几年,所以它能做得很精致,但蛛网差不多只用一个小时就造成了,所以它只能做出这种曲线的一个轮廊,管不精确,但这确实是算得上一个螺旋曲线。是什么东西在指引着它呢?除了天生的技巧外,什么都没有。天生的技巧能使动物控制自己的工作,正像植物的花瓣和小蕊的排列法,它们天生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教它们怎么做,而事实上,它们也只能作这么一种,蜘蛛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练习高等几何学,靠着它生来就有的本领很自然地工作着。
我们抛出一个石子,让它落到地上,这石子在空间的路线是一种特殊的曲线。树上的枯叶被风吹下来落到地上,所经过的路程也是这种形状的曲线。科学家称这种曲线为抛物线。
几何学家对这曲线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假想这曲线在一根无限长的直线上滚动,那么它的焦点将要划出怎样一道轨迹呢?答案是:垂曲线。这要用一个很复杂的代数式来表示。如果要用数字来表示的话,这个数字的值约等于这样一串数字+1/1+1/1*2+1/1*2*3+1/1*2*3*4+……的和。
几何学家不喜欢用这么一长串数字来表示,所以就用“e”来代表这个数。e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数学中常常用到它。
这种线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呢?并不,你到处可以看到垂曲线的图形:当一根弹性线的两端固定,而中间松驰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条垂曲线;当船的帆被风吹着的时候,就会弯曲成垂曲线的图形;这些寻常的图形中都包含着“e”的秘密。
一根无足轻重的线,竟包含着这么多深奥的科学!我们暂且别惊讶。一根一端固定的线的摇摆,一滴露水从草叶上落下来,一阵微风在水面拂起了微波,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极为平凡的事,如果从数学的角度去研究的话,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我们人类的数学测量方法是聪明的。但我们对发明这些方法的人,不必过分地佩服。因为和那些小动物的工作比起来,这些繁重的公式和理论显得又慢又复杂。难道将来我们想不出一个更简单的形式,并使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吗?难道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让我们不依赖这种复杂的公式吗?我相信,越是高深的道理,其表现形式越应该简单而朴实。
在这里,我们这个魔术般的“e”字又在蜘蛛网上被发现了。在一个有雾的早晨,这粘性的线上排了许多小小的露珠。它的重量把蛛网的丝压得弯下来,于是构成了许多垂曲线,像许多透明的宝石串成的链子。太阳一出来,这一串珠子就发出彩虹一般美丽的光彩。好像一串金钢钻。“e”这个数目,就包蕴在这光明灿烂的链子里。望着这美丽的链子,你会发现科学之美、自然之美和探究之美。
几何学,这研究空间的和谐的科学几乎统治着自然界的一切。在铁杉果的鳞片的排列中以及蛛网的线条排列中,我们能找到它;在蜗牛的螺线中,我们能找到它;在行星的轨道上,我们也能找到它,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原子的世界里,在广大的宇宙中,它的足迹遍布天下。
这种自然的几何学告诉我们,宇宙间有一位万能的几何学家,他已经用它神奇的工具测量过宇宙间所有的东西。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我觉得用这个假设来解释鹦鹉螺和蛛网的对数螺线,似乎比蠕虫绞尾巴而造成螺线的说法更恰当。
条纹蜘蛛
不管是谁,大概都不会喜欢冬季。在这个季节里,许多虫子都在冬眠。不过这并不说明你没有什么有虫子可观察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观察者在阳光所能照到的沙地里寻找,或是搬开地下的石头,或是在树林里搜索,他总能找到一种非常有趣的东西,那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那些有幸欣赏到这艺术作品的人真是幸福。在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发现这种艺术品的喜悦使我忘记了一切不快,忘记了一天比一天更糟的气候。
如果有人在野草丛里或柳树丛里搜索的话,我祝福他能找到一种神秘的东西:这是条纹蜘蛛的巢。正像我眼前所呈现的一样。
无论从举止还是从颜色上讲,条纹蜘蛛是我所知道的蜘蛛中最完美的一种。在它那胖胖的像榛仔仁一般大小的身体上,有着黄、黑、银三色相间的条纹,所以它的名字叫“条纹蜘蛛”。它们的八只脚环绕在身体周围,好像车轮的辐条。
几乎什么小虫子它都爱吃。不管那是蝗虫跳跃的地方还是苍蜂盘旋的地方,是蜻蜓跳舞的地方还是蝴蝶飞翔的地方。只要它能找到攀网的地方,它就会立刻织起网来。它常常把网横跨在小溪的两岸,因为那种地方猎物比较丰盛。有时候它也在长着小草的斜坡上或榆树林里织网,因为那里是蚱蜢的乐园。
它捕获猎物的武器便是那张大网,网的周围攀在附近的树枝上。它的网和别种蜘蛛的网差不多:放射形的蛛丝从中央向四周扩散,然后在这上面连续地盘上一圈圈的螺线,从中央一直到边缘。整张网做得非常大,而且整齐对称。
在网的下半部,有一根又粗又宽的带子,从中心开始沿着辐一曲一折,直到边缘,这是它的作品的标记,也是它在作品中的一种签名。同时这种粗的折线也能增加网的坚固性。
网需要做得很牢固,因为有时候猎物的份量很重,它们一挣扎,很可能会把网撑破。而蜘蛛自己不会选择或捕捉猎物,所以只能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大网以捕获更多的猎物。它静静地坐在网的中央,把八只脚撑开,为的是能感觉到网的每一个方向的动静。摆好阵势后,它就等候着,看命运会赐予它什么:有时候是那种微弱到无力控制自己飞行的小虫;有时候是那种强大而鲁莽的昆虫,在做高速飞行的时候一头撞在网上,有时候它好几天一无所获,也有时候它的食物会丰盛得好几天都吃不完。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白天隐居的蜘蛛们的网,我们可以看到从网中心有一根丝一直通到它隐居的地方,这根线的长短大约有二十二寸;不过角蛛的网有些不同,因为它们是隐居在高高的树上的,所以它的这根丝一般有八九尺长。
这条斜线还是一座桥梁,靠着它,蜘蛛才能匆匆地从隐居的地方赶到网中,等它在网中央的工作完毕后,又沿着它回到隐居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就是这根线的全部效用。如果它的作用仅仅在于这些的话,那么这根线应该从网的顶端引到蜘蛛的隐居处就可以了。因为这可以减小坡度,缩短距离。
这根线之所以要从网的中心引出是因为中心是所有的辐的出发点和连接点,每一根辐的振动,对中心都有直接的影响。一只虫子在网的任何一部分挣扎,都能把振动直接传导到中央这根线上。所以蜘蛛躲在远远的隐蔽处,就可以从这根线上得到猎物落网的消息。这根斜线不但是一座桥梁,并且是一种信号工具,是一根电报线。年轻的蜘蛛都很活泼,它们都不懂得接电报线的技术。只有那些老蜘蛛们,当它们坐在绿色的帐幕里默默地沉思或是安详地假寐的时候,它们会留心着电报线发出的信号,从而得知在远处发生的动静。
长时间的守候是辛苦的,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和好好休息。同时又丝毫不放松对网上发生的情况的警觉,蜘蛛总是把腿搁在电报线上。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曾经打到一只在两棵相距一码的常青树间结了一张网的角蛛。太阳照得丝网闪闪发光,它的主人早已在天亮之前藏到居所里去了。如果你沿着电报线找过去,就很容易找到它的居所。那是一个用枯叶和丝做成的圆屋顶。造得很深,蜘蛛的身体几乎全部隐藏在里面,用后端身体堵住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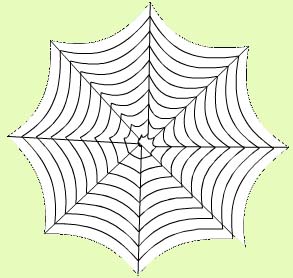 |
蛛网的建筑
即使在最小的花园里,也能看到园蛛的踪迹。它们都算得上是天才的纺织家。
如果我们在黄昏的时候散步,我们可以从一丛迷迭香里寻找蛛丝马迹。我们所观察的蜘蛛往往爬行得很慢,所以我们应该索性坐在矮树丛里看。那里的光线比较充足。让我们再来给自己加一个头衔,叫做“蛛网观察家”吧!世界上很少有人从事这种职业,而且我们也不用指望从这行业上嫌点钱。但是,不要计较这些,我们将得到许多有趣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从事任何一个职业要有意思得多。
|
我所观察的都是些小蜘蛛。它们比成年的蜘蛛要小得多。而且它们都是在白天工作,甚至是在太阳底下工作的,尽管它们的母亲只有在黑夜里才开始纺织。当到每年一定的月份的时候,蜘蛛们便在太阳下山前两小时左右开始它们的工作了。
这些小蛛都离开了它们白天的居所,各自选定地盘,开始纺线。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谁也不打扰谁。我们可以任意地拣一只小蛛来观察。
让我们就在这只小蛛面前停下吧。它正在打基础呢。它在迷迭香的花上爬来爬去,从一根枝端爬到另一根枝端忙忙碌碌的,它所攀到的枝大约都是十八寸距离之内的。太远的它就无能为力了。渐渐地它开始用自己梳子似的后腿把丝从身体上拉出来,放在某个地方作为基底,然后漫无规则地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这样奔忙了一阵子后,结果就构成了一个丝架子。这种不规则的结构正是它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垂直的扁平的“地基”。正是因为它是错综交叉的,因此这个“地基”很牢固。
后来它在架子的表面横过一根特殊的丝,别小看这根细丝,那是一个坚固的网的基础。这根线的中央有一个白点,那是一个丝垫子。
现在是它做捕虫网的时候了。它先从中心的白点沿着横线爬,很快就爬到架子的边缘,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回到中心,再从中心出发以同样的方式爬到架子边缘,就这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每爬一次便拉成一个半径,或者说,做成一根辐。不一会儿,便这儿那儿地做成了许多辐,不过次序很乱。
无论谁,如果看到它已完成的网是那么地整洁而有规则,一定会以为它做辐的时候也是按着次序一根根地织过去,然而恰恰相反,它从不按照次序做,但是它知道怎样使成果更完美。在同一个方向安置了几根辐后,它就很快地往另一个方向再补上几条,从不偏爱某个方向,它这样突然地变换方向是有道理的:如果它先把某一边的辐都安置好,那么这些辐的重量,会使网的中心向这边偏移从而使网扭曲,变成很不规则的形状。所以它在一边安放了几根辐后,立刻又要到另一边去,为的是时刻保持网的平衡。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像这样毫无次序又是时时间断的工作会造出一个整齐的网。可是事实确实如此,造好的辐与辐之间的距离都相等,而且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圆。不同的蜘蛛网的辐的数目也不同,角蛛的网有二十一根辐,条纹蜘蛛有三十二根,而丝光蛛有四十二根。这种数目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是基本上是不变的,因此你可以根据蛛网上的辐条数目来判定这是哪种蜘蛛的网。
想想看,我们中间谁能做到这一点:不用仪器,不经过练习,而能随手把一个圆等分?但是蜘蛛可以,尽管它身上背着一个很重的袋子,脚踩在软软的丝垫上,那些垫还随风飘荡,摇曳不定,它居然能够不加思索地将一个圆极为精细地等分。它的工作看上去杂乱无序,完全不合乎几何学的原理,但它能从不规则的工作中得出有规则的成果来。我们都对这个事实感到惊异。它怎么能用那么特别的方法完成这么困难的工作呢?这一点我至今还在怀疑。
安排辐的工作完毕后,蜘蛛就回到中央的丝垫上。然后从这一点出发,踏着辐绕螺旋形的圈子。它现在正在做一种极精致的工作。它用极细的线在辐上排下密密的线圈。这是网的中心,让我们把它叫作“休息室”吧。越往外它就用越粗的线绕。圈与圈之间的距离也比以前大。绕了一会,它离中心已经很远了,每经过一次辐,它就把丝绕在辐上粘住。最后,它在“地基”的下边结束了它的工作。圈与圈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有三分之一寸左右。
这些螺旋形的线圈并不是曲线。在蜘蛛的工作中没有曲线,只有直线和折线。这线圈其实是辐与辐之间的横档所连成的。
以前所做的只能算作是一个支架,现在它将要在这上面做更为精致的工作。这一次它从边缘向中心绕。而且圈与圈之间排得很紧,所以圈数也很多。
这种工作的详细情形很不容易看清,因为它的动作极为快捷而且振动得很厉害,包括一连串的跳跃、摇摆和弯曲,使人看得眼花缭乱。如果分解它们的动作,可以看到它的其中两条腿不停地动着,一条腿把丝拖出来传给另外一条腿,另一条腿就把这丝安在辐上。由于丝本身有粘性,所以很容易在横档和丝接触的地方把新技出来的丝粘上去。
蜘蛛不停地绕着圈,一面绕一面把丝粘在辐上。它到达了那个被我们称作“休息室”的边缘了。于是它立刻结束了它的绕线运动。以后它就会把中央的丝垫子吃掉。它这么做是为了节约材料,它下一次织网的时候就可以把吃下的丝再纺出来用了。有两种蜘蛛,也就是条纹蛛和丝光蛛,做好了网后,还会在网的下部边缘的中心织一条很阔的锯齿形的丝带作为标记。有时候,它们还在这一条丝带的封面,就是网的上部边缘到中心之间再织一条较短的丝带,以表明这是它们的作品,著作权不容侵犯。
节选于《昆虫记》,[法]j.h.法布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