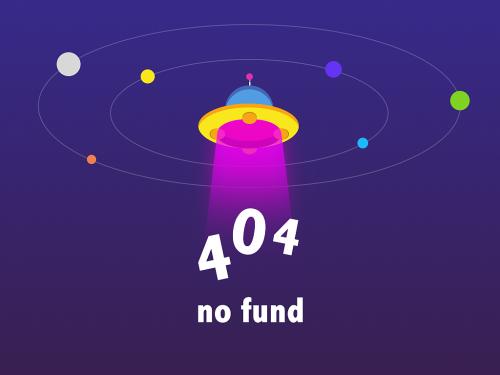
关于作者
吴玉虎, 男,1951年1月16日生,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长;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 中国植物专家组(cpsg)成员;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和植物区系地理以及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工作,在高原、高山植物的生态、区系地理及豆科和禾本科植物的分类方面有较深研究。
逃出“死亡谷”
吴玉虎
2010年11月22日病中艰难路——歧路逢险境——逃出“死亡谷”——进退两难
次日起来,我仍腹痛不止。拆帐篷,绑行李,浑身没劲,早饭也没吃,只是用开水冲了一点麦乳精强迫自己喝下。
有气无力地爬上了驼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莫莫克的杏林,继续我们漫长的旅途。今天沿途的景观和昨天的大致相同,驼队在烈日曝晒下艰难地走了6个多小时,才爬上了山顶。途中一峰白毛骆驼因天热负重而曾在半山腰卧倒了七八次,任驼工怎么打,怎么拉,它也不愿起来,只是不停地扬头大叫,以示抗议。看来是因山太陡而爬不动了,每次都得几个驼工帮它才勉强起来。最后,只得给它减轻一些东西加在别的骆驼背上,才稍好一点。在光秃秃的山顶休息并午餐时,除了腹部不时仍有阵阵隐痛外,我又增加了头晕的感觉,而且仍不想吃任何东西,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想躺下睡去。有人送来了西瓜也不屑一顾而婉言谢绝——尽管这时的天是那样地热,汗是那样地多,而且口又是那样地渴。
下山的路更是难走。仅有的一条路,也正是洪水流经之道。匀细的荒漠沙壤土路面,被水冲成了一条大沟,有的地方竟深过两米,骆驼就走在距沟的边缘约20~30厘米的地方。一旦踏空或沟边塌方,骆驼就有折断腿的危险,而人也将无疑会被摔伤,还有许多地方的路,需要费好长时间垫平了沟才能通行。然而,却并没有出什么意外,看来,骆驼走这种路似乎也很有经验。
再往下走,坡更陡了,人已不宜骑在骆驼上了,大家都早已下来步行,就连骑毛驴的老驼工也都下地来,一边牵着毛驴,一边像螃蟹样地横着身体顺山坡往下挪步。只有我还高高在上地骑在驼背上。由于浑身无力,我原本打算今天是无论如何也不下骆驼的,但是我却越走越心虚,因为山披已陡得有时连骆驼都直往下滑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由人扶着下驼步行。
若在平时,这并没什么,我会早早就下来的,并会因此而自由许多,也用不着担心骆驼踩空,又可以边走边看路边的植物,并顺手采些标本,而且还可以在事先看好大方向的前提下抄近道走,因为我经常这样干。可今天就不同了,昨夜拉了四次肚子,今晨到现在仍空着肚子,况且还有些感冒,头痛得厉害,可能还在发烧,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可真苦了我了。
由于山高坡陡,下山本来就不好受,一步一颠,膝盖被颠得难受,一直传到我晕眩的头部,脑后部分似炸裂般地不断受到震动,两腿实在难以抬起。然而,双脚一旦抬起,落下时却很快,并且是不用大脑指挥的。如果说每抬一步似需千钧之力的话,而每落一步则又似醉汉被人从背后暗算了一闷棍而东倒西歪,深浅不知。就这样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着,直到连摔了两跤才打起精神来。
走下一个山头,职业的本能使我不时地还要采集几份标本。不知不觉地倒忘记了自己的体弱头晕,而被眼前的植物引离了原路。绕行的驼队已被摔在后面,只有马鸣距我较近,于是同他商量,先看了看周围地形,确定了大方向后我们选择了一条“近道”直下山去,以求节省一些体力并采些标本。殊不知,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却是祸不单行,而前面竟是绝路。待我们下到沟底,对面的山坡竟上不去,原先看到对面山上的一条路,也已仿佛挂在半天,而沟底却是由洪水冲刷而崩塌形成的绝壁。抬头回望来路,五六百米垂直高度的大山,可不是好上的,不用说已经体力不支,一想,我就泄了气。
后退既然已不可能,那索性就来个一错到底。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稍斜的坡,我用匕首挖脚窝开路,3米多高的陡坡,小马帮我一步一个脚窝地上到了顶部,留他在沟底继续探路。我越过坡顶,坡那边又是十几米深的断崖。于是我顺着坡顶朝下山的方向走去,想找一处缓坡下到另一边的沟底,却没有成功。
坡顶越来越窄,而两边的冲沟则越来越深。到后来,有一段约6米多长的坡顶竟不足40厘米宽,两边的沟深却有30多米,除了中下部的坡度在60~80度外,其顶部约有近3米高的的一截竟是垂直的90度,恰似山顶上的一堵“墙”,但却没有墙体那样坚牢。平时在两米多高的墙头几乎可以迅跑的我,此时此地却不由得两脚有些微微发抖,身体也有些摇晃,不敢往两边看,甚至讨厌眼睛射向两边的余光。无奈,只走了两米多远就不得不弯下身来,骑马式地爬过去。心想,如果这又潮又虚的土“墙”塌方的话,???? 无论倒向哪一边,我都可以用手抓另一边而不致于掉下,滚落到深达30米的沟底。但这也只能是当时无可奈何情况下的一种愿望而已。试想,在雨水浸淋过不久的湿沙土上,约40厘米宽的土体能有多大的支持力,对于一个50多公斤重的人来说,再加上突然跌下的重力和冲力,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所以,我连大气也不敢出。好在由于重心降低了,再加之我又小心翼翼地不敢有半点疏忽,最后总算顺利地爬了过去——尽管两边都有沙土落下。
再前面,开始下坡了,且坡顶越来越宽,我提起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是应该出一口长气的时候了。不料,高兴得太早,最前面竟然也是断崖一面,而两边的冲沟已合成了一条,我被困在几乎是四面绝壁的孤岛上。原地转了一圈后,我竟下意识地把眼睛投向了天空。多么荒唐可笑的举动,难道在这入地无门的此地此时会有上天之路吗?其实,这不由自主的一眼,是在看什么,连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在异想天开地寻找一架飞机吧,而且是一架直升飞机。看来,人在绝望之时,或许都会异想天开吧。不过,我觉得我还远不到那一步。但我忽然又觉得似乎有些胆怯,于是大喊马鸣,直到第三声,他才答应,并且是在距我不远处的沟底。此时,我迫不得已地向后转,尽管在土“墙”处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头皮第二次创造了“奇迹”,顺原路下到沟底。
刚才上陡坡时的刀坑脚窝“路”,下来时,竟成了滑梯。原来是在踩着脚窝并用刀子扎入土中借力时,刀子竟扎在了一块石头上,又加上用力过猛,身子一仰,脚下本能地一使劲,脚窝塌了。人整个胸腹部贴着坡壁迅速滑到沟底,糊里糊涂就跌坐在地上。不过,除了腹部和两手掌稍擦破点皮外,竟没有摔伤。再看坡面上,除身体下滑的痕迹外,尚有一条用刀尖划出的细缝。好在沟底是湿泥地,只不过弄湿了裤子有些冰凉罢了。
找到马鸣,一同顺沟而下,又爬着“享受”了两次“滑梯”。冲沟两边的山体起初不过三五米高,且冲沟显得较宽敞,可是越往下走,沟就越深,且时宽时窄,最窄处竟不及一米,由于两边土崖的高度,而致抬头仅见一线天,使得光线阴暗,泥土潮湿,空间缩小,又加之万籁俱寂,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我又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此时的我,害怕危险的心理恐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我的嘴里念叨着:“这是鬼谷,死亡之谷。”以此来提醒自己应设法尽快离开这鬼地方,绝不愿多呆那怕是一秒钟。尽管我们的“前途”未卜,谁也不知道距这条冲沟的终点有多长,又在那里,也不知顺着冲沟走去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还是一味地向下游方向前进着。
如果说刚才在爬过断崖土“墙”时,我还有几分主动权的话,那么,现在的处境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因为两边的土崖上还在刷刷地往下掉土,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保不住那一块崖壁会突然塌下而将我们埋在下面。但在当时,我竟还出现过一个一闪即过的念头:在这里留下一张影,记录下这次的险境实景,或是给其他人留下个警告。然而,这个念头在出现的同时就被果断地否定了,因为我已听到前方似乎有塌方的声音。
我们开始迅跑起来。由于冲沟弯弯曲曲,而且沟底时有洪水过后新添的塌方虚土未被冲走而高低不平,因而一前一后奔跑的我俩,活像被持枪者追杀的逃犯或是被狼群尾随的猎物一般心急嫌脚慢。时而疾步于稍干而平缓的沟底;时而跳过较小的泥潭水洼;时而又滑下不太高的洪水瀑布曾经之地,借以温习小儿时代就该熟悉了的滑梯游戏;又时而翻越塌方形成的虚土堆,时而全身面壁贴墙呈“大”字形挂在崖壁上并借助匕首的力量保持平衡,寸寸移步于较大泥塘的边缘;时而又无奈地艰难跨涉于沼泽般的泥水中,双脚陷入水下泥淖中有半尺多深,但裤子却不随脚而下,提起来装满两鞋泥浆。曾几次被泥水吸住了鞋而光脚拔起,再回头从泥沼中摸出鞋穿上继续前进。至于膝盖以下的两腿和双脚全都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泥浆套而不见裤子和鞋的影子等,已是太小的小事而顾不上理会了,唯恐自己的动作慢半拍。病似乎也没有了,且体力和精神俱佳。但是,我怎么也跑不过马鸣。由于看不见远在前面的马鸣,难免心里发毛。我曾几次想大喊马鸣,让他跑慢点或干脆等我一块跑,但是却终究未敢出声。因为我怕太大的声音会引起塌方。
如此奔命约有半个多小时,冲沟才渐宽起来,已经接近了河谷地带,我们一直提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了头顶上方有驼铃声,两人同时像小孩一样情不自尽地大喊:“我们出来了,我们逃出了鬼谷!”当时的激动使得我们多少有些失态。
等见了大家,我俩没事人似的,极力表现出应有地平静,生怕有人看出我们刚才的心虚、紧张和失态来。岂不知40多分钟前加快的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所出的汗也还没有完全落下呢。虽然我们拖着泥糊糊的两腿和一身的狼狈相,但这在野外考察中是司空见惯的,因而不会引起大惊小怪的。
回想刚才的半小时,真是集长跑、冲刺、跨栏、跳远、登高、技巧等运动项目于一身的全能运动。这30分钟是精神高度集中的30分钟,是体力最佳、体能最佳、竟技状态最佳、判断力最佳、处理问题最决断且效果最佳的30分钟,因而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30分钟,只可惜少了一张纪念照。
上骆驼后,顺河谷而上,这一天骆驼也够累的,上山,下山,现在又行走在河滩卵石间。这一带沿河两岸住着一些半农半牧的维吾尔族老乡,正是庄稼收割后的打场季节,许多老乡都站在路边,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的驼队。傍晚10时许,我们借宿在一个名叫铁盖奇的小村里。
一躺下来,我便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遍体筋骨酸痛。尽管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但现在仍是不思饮食,且头痛欲裂,发烧到38.5 ,腹痛欲泻而又无物可泻,几次起来又躺下。起身时竟觉浑身酸软无力,甚至有不借助他人的帮助而无法起身的感觉。心想,下午在“死亡谷”中还能奋力跑跳奔驰,何至于到现在这种连翻个身都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在大家的劝说下,临睡前强迫自己吃了些挂面,但不一会就全都吐了出来。看样子,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愈来愈重之趋势,只好不断加大药量来控制病情。随后再次强咽下一小块维吾尔族老乡家的馕饼和一大碗滚烫的茯茶水,然后便昏沉沉地躺着。
从昨晚到现在,由于我的病情时渐严重,使全组人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有心让我继续随队前进吧,生怕随着海拔的升高,气候越来越恶劣,饮食和医药条件越来越差而耽误了我的病,因为这在野外考察中是有过先例的。送我返回叶城县吧,又怕路途艰难,照顾不周时还不如和大家在一起的好。只恨此地山高水远却不通公路。
武副队长和老冯、武云飞等相商着还是打算找几个当地老乡和组里的一个人把我送回叶城县,我却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经过一天的“饥饿疗法”,在有营养补充的条件下,这点病根本算不了什么,我肯定能挺过去。当知青的年代和以往十几年的考察中也有过类似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我都平安地挺过来了,这次也不应例外。再说,不离开集体,就不会失去大家的关心和照顾,更何况,武副队长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最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大家决定还是让我继续随队前往考察。